

梁帝壽宴,以蒞陽長公主首告,霓凰以林家遺屬,蔡荃、沈追、柳澄為首的百官一句句振聾發聵的「臣附議」,到紀王、穆青、言闕、景琰等相繼奏請梁帝重審赤焰軍一案,再加上靖王已經掌控最關鍵的軍權,梁帝不得不下旨同意重審,而這標志著梁帝的主動認錯,更標志著一代皇權的更迭。
皇宮內院,以前的靜妃,如今的太后,曾經的太子妃,如今的皇后,帶著皇子玩鬧嬉戲,已經長大,且被靖王,如今的皇上收為義子的庭生迎面走來,很快兩個孩子玩得不亦樂乎,而站在一側的高公公,笑容滿面地望著這一切,風驟起,高公公咳了起來,聞聲,皇后關心地囑托高公公多添衣物。
高公公,伺候梁帝幾十年,深受梁帝信任,靖王繼位后,他又平穩地依舊伺候在側,且同樣備受重視,在爾虞我詐的后宮風云之中、在波詭云譎的朝廷之上,在伴君如伴虎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帝王之側,高公公高湛最終得了善終。

作為深受梁帝信任,且幾乎是唯一信任的貼身太監,在梅長蘇為赤焰軍洗刷冤屈的步步為營里,但凡高公公輕而易舉地向梁帝說上一句不利的話,梅長蘇的計謀很大可能就不會得逞,他,其實才是梅長蘇真正忌憚的人,而重溫《瑯琊榜》,我才懂高公公的精明,更懂他骨子的情與義,活該他笑到了最后。
皇宮之內,權力最為集中,爭權逐利也最為赤裸裸,為了權為了利,更為了那至高無上的寶座,各方勢力盤根錯節,又各自為營各有算計,而高公公,只守好了自己的本分。
他的守本,體現在兩點。

一是守好本心。
高公公雖身在皇宮,泡在最復雜和最殘酷的權力染缸里,但他依舊保持了一個人內心本有的善良。
靖王換防回宮面見陛下,此時梁帝、太子和譽王正在欣賞字畫,等了一個多時辰后,他借給梁帝收拾桌子時提醒了梁帝;穆霓凰因招親在京城待了很久,梁帝問高公公有多長時間了,高公公并不認為很久說「尚未一年」,梁帝不滿后他又改口「已經一年」;太子因私炮房爆炸事件被禁東宮備受冷落,恰逢太皇太后仙逝,太子在宮中尋歡作樂,梁帝前去探望,慌亂的太監讓梁帝起了疑心,高公公趕緊詢問是否讓太子出來接駕試圖為太子解困;譽王聯合慶歷軍謀逆,梁帝說譽王終究是玲瓏公主的兒子,高公公安慰梁帝事情或許沒有想象得那麼糟糕,為譽王留了一絲余地。
為靖王、為霓凰、為太子、為譽王…...各方勢力間,他都為他們說上一句最得體,最發自本心的話,都出自他的一份善心。
皇宮之中,不刻意偏袒,卻又在人之常情里保留一份作為人最該有的真摯,說一句內心最真誠的話,對于無情的帝王之家、對于殘酷的宮廷爭斗,高公公的這份真與善,尤顯珍貴。

二是做好本職。
高公公是梁帝身邊的貼身太監,他的工作就是伺候好梁帝、保護梁帝的隱私、討梁帝歡喜、做符合梁帝脾氣的事。
所以,當梁帝因煩惱太子和譽王為爭巡防營焦頭爛額,又被殿門外的蟬聲吵得不厭其煩時,他順梁帝之意叫太監們趕緊捕蟬;所以,譽王的生母祥嬪,實為滑族玲瓏公主的秘密只有梁帝和高公公知曉,但高公公一直嚴守秘密;所以,但凡宮中有人,甚至是梁帝自己提及林燮、宸妃等人,他都一副懼怕而不敢言的樣子,他知道這些都是梁帝的忌諱;所以,他與宮中各皇子、權貴,甚至是后宮妃嬪,從無半點交往甚密,他雖身在權力中心卻始終獨立于權力之外。
只因為,他深懂梁帝之脾性。

正如梅長蘇對靖王說過的:
要說這世上誰最了解皇上的心思,那絕不是皇后和越貴妃,也不是太子和譽王,而是這位高公公。
因為了解,所以懂得如何做,懂得了如何做,就能在這萬般兇險中,找到最關鍵的保命之路,對于高公公而言,他做所有事情的出發點都皆以梁帝的所思所想為準則,甚至做梁帝想做又在明面上不能做的事,而這,是他的本職,而他,也做得足夠好。

我始終覺得,作為一介備受帝王信任幾十年的貼身太監,在各種權力爭奪中,他的地位其實是舉足輕重的,也幾乎是各方勢力都愿意拉攏的對象,可高公公從不主動攀附任何權貴,也不受任何勢力侵蝕,而是在最容易被沾染私欲之氣的地方,做了一個有溫度、有主見,更有智慧的身邊人和中間人。
高公公,歷經三朝,最后得以善終,他或許比其中的任何一人都見得多,也懂得多,尤其是奪嫡之爭。
起初,太子景宣和譽王景桓,最炙手可熱,景宣,作為太子,是最得寵的越貴妃之子,有一品軍侯寧國侯謝玉坐鎮,朝中戶部、禮部、兵部聽其所令,而譽王,作為言皇后的養子,軍中有慶國公,朝中有吏部、刑部、工部為其馬首是瞻,兩方勢均力敵,又斗得如火如荼。
瑯琊榜首,「麒麟才子」梅長蘇以休養為名進京后,表面輔佐譽王而挑起與太子之間的爭斗,又暗自折兩方人馬逐漸將最不得寵的靖王推向奪嫡的舞台,朝局在梅長蘇的步步謀劃中,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而這場奪嫡之爭,高公公至少看透了兩點。
一是看透了人。
梁帝之下,只有景宣、景桓和景琰三人有望繼承皇位,而誰最合適,沒有人比高公公還清楚。
景宣,雖是太子,但軟弱無能,因其名下的私炮房爆炸被梁帝禁足東宮,卻又不思悔改,在太皇太后喪禮期間,大肆飲酒尋歡作樂被梁帝廢去了太子之位,而封了獻王;景桓,雖是梁帝最為寵愛、也是最像梁帝的兒子,他同樣可以因與太子私斗引爆私炮房致69人喪命,但因其身份是滑族玲瓏公主的兒子,其實就已經決定了他不可能坐上大梁的皇帝之位。
一個可以坐,卻被自己的無能把皇位作沒了;一個不能坐,卻因不甘心而寧死也要造反把自己的命作沒了。

而靖王,他自幼跟在祁王身邊,頗有祁王之風,他始終相信赤焰軍和祁王的忠誠,又在為太皇太后守喪期間,他不改軍人之姿,筆直跪著不偷偷吃食以盡孝道.
靖王常年整軍、征戰在外,他骨子里不愿妥協的情義,和異于其他皇子的姿態與正義之氣,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
雖靖王脾氣耿直,不懂權謀,但比起太子的無能、譽王的草菅人命,靖王,才是真正可為民、有人情的繼位者,作為局外人,也是局中人的高公公,他心中的稱會偏向誰,不言而喻。

二是看透了勢。
這個「勢」,是形勢。
靖王調查完慶國公濱州侵地案后向梁帝上奏案情,梁帝對執筆寫案文的刑部主司蔡荃一陣夸獎,后因刑部換囚案,以刑部尚書為首的眾多官員被牽涉其中,刑部一團亂,對于任命誰為刑部尚書,梁帝詢問靖王意見,并從靖王提及的侵地案中想到了當時寫結案文書的人,并問身旁的高公公叫什麼名字,而高公公只是嘿嘿地笑,靖王接話回答是蔡荃,并說以他的了解,蔡荃應該不會涉換囚案中。
高公公與梁帝形影不離,他不可能不記得,只不過有靖王在場,他不涉朝局而選擇不言,而靖王的一句「以我對他的了解」,高公公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靖王,他已然知曉: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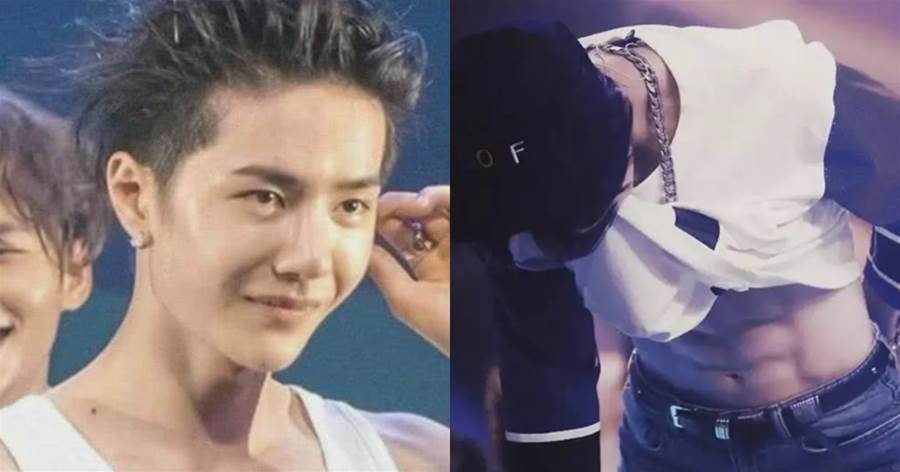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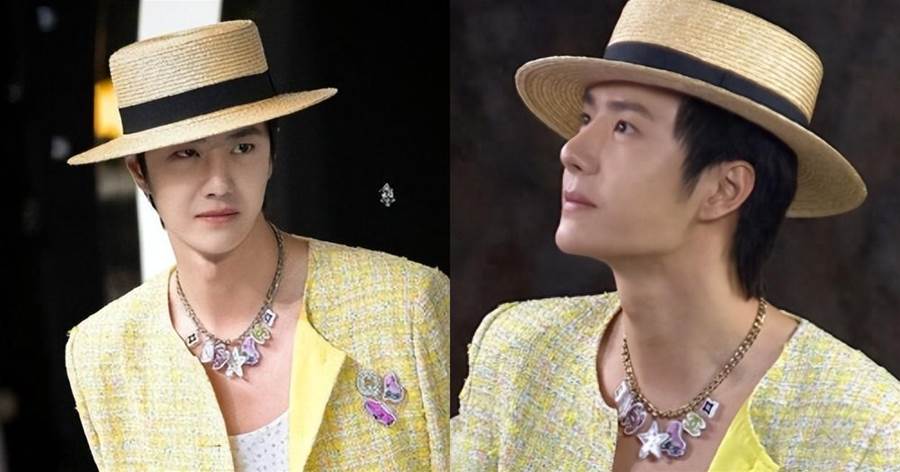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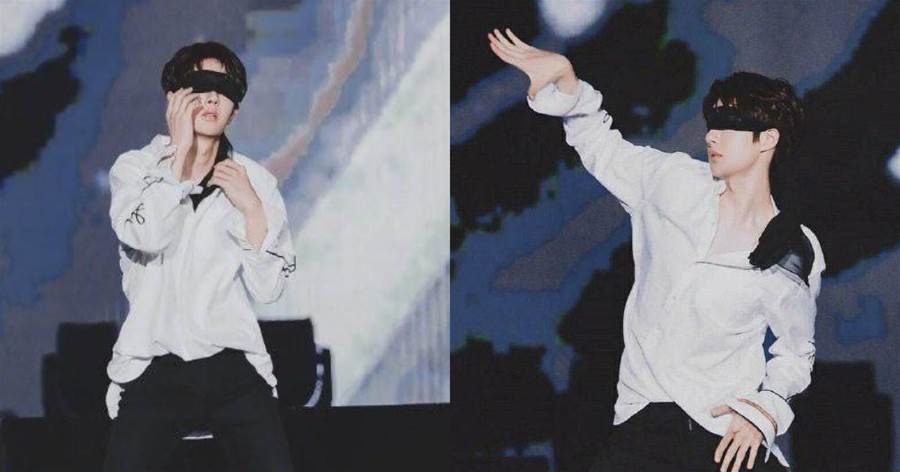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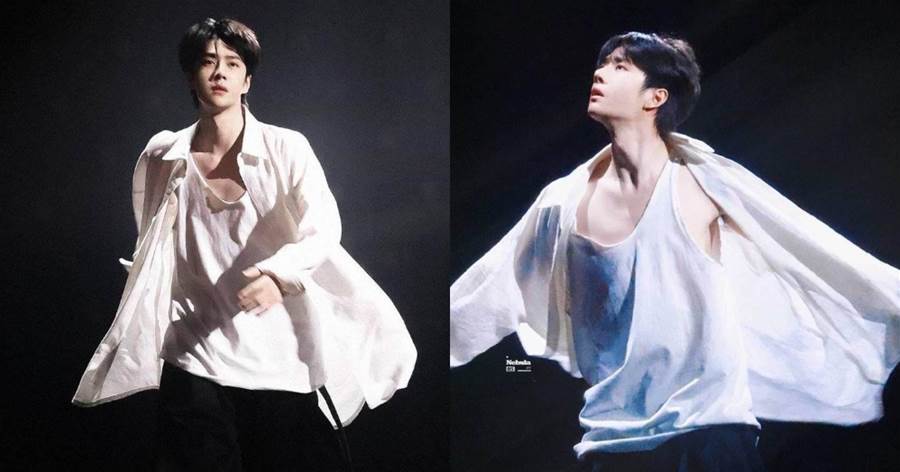





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