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前言
少商和霍不疑的婚禮來臨了,只是貌似這洞房花燭夜有些不尋常。
【恐婚的程少商】
辰時,程少商便被蓮房從睡夢中拉了起來。
醉眼迷糊的她,央求著:「好蓮房,你再讓我睡會。」
蓮花焦急地說著:「女公子,今日是你成親的大喜日子,怎可貪睡呢?」
程少商迷迷糊糊地說著:「蓮房你莫要誆我,婚禮要申時才開始。」
「雖是申時才開始,可我們要早早準備的。沐浴、更衣、梳妝、拜別父母,好多繁瑣的程序要走一遍呢?」
「我們在驊縣成親,迎娶嫁婦皆是在一處,怎麼還會有這般繁瑣的流程呢?」程少商搖搖晃晃地坐在床上,揭穿小丫鬟的話。
「姑爺說,雖說在驊縣成親,但也要讓女公子風光大嫁,絕不會委屈女公子。」
「蓮房,你現在就開始姑爺姑爺地喚著了,說,霍不疑給了你什麼好處。」程少商嘟著小嘴問道。
「天地良心,蓮房一心一意只為女公子,絕無二心。」蓮房跪在床榻之上,豎著手指發誓。
程少商按下了蓮房的小手,笑著道:「逗你玩呢,你讓我再睡一會兒,我保證,絕對不會耽誤事情。」
說完,程少商便栽倒在床上,繼續補眠。
蓮房吃力地再次將程少商拉了起來,可憐巴巴地說著:「女公子,你快醒醒吧,就當是可憐可憐我,女君還等著為您梳頭呢。若是遲了,非罵我不可。」
「不會的,我阿母現在可溫柔了呢。」程少商沒心沒肺地笑著,想著最近變化巨大的阿母,她嘴角揚起了一絲絲的笑意。
咯……
在蓮房的拉扯之中,程少商打了一個酒嗝,酒味撲面而來。
蓮房驚慌失措地說著:「女公子,你昨夜喝酒了?」
少商點了點頭,比劃著:「只喝了一點點。
」
「這還一點點呢,我都聞到酒味了。天呀,若是被女君知曉了,定是要挨罵的。」
程少商自信地說著:「放心,有霍不疑在,阿母不會罵我的。」
「女公子,那您也不該喝酒的。」蓮房委屈地說著。
「蓮房,你不懂,馬上就要成親了,我害怕。」程少商逐漸地清醒過來,弱弱地說著。
「這世間還有女公子害怕的事情不成?想當年,我們遇見了那麼多困難,女公子從未怕過。」蓮房想起女公子當年的壯舉,自信地說著。
「不一樣的,女子成親,便是第二次投胎。」
「姑爺對女公子這般好,女公子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?」蓮房不解地問道。
「霍不疑對我是極好,可,萋萋阿嫂說洞房會痛,懷孕會痛,生娃會痛,當了人家阿母,更是渾身不自由。」程少商托著腮,茫然無知地說著:「自古以來,母雞下蛋,公雞打鳴,我以為女人生孩子,要男人何用?如今才知,這女人生孩子,是這般痛楚,想想就可怕。」
蓮房笑著道:「女公子,您說得就像您生過娃一般。」
「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,雖說我沒生過,可是萋萋阿嫂生過呀。」程少商倔強地說著。
「程少夫人之所以會疼,是因為生了雙胎的緣故,女公子不必怕,你和她不一樣。」蓮房安慰著程少商。
「哎,萬一我生的也是雙胎怎麼辦?他們說呀,子隨母,我和三兄便是雙胎。」蓮房的安慰,不但沒有寬慰到少商,反而引起了少商的恐慌。
蓮房蹙著眉,試探性地問道:「女公子,您是不是有些害怕成親呀?」
「好像是呀,怎麼辦?」程少商可憐兮兮地說著。
蓮房拉著程少商的胳膊,將她拉下了床,安慰道:「您閉上眼睛什麼都不要想,將一切交給蓮房,忍一忍便過去了。
」
程少商看著蓮房可愛的模樣,不自覺地嘴角洋溢著笑容。其實,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?明明很期待嫁給他,可是,真到了成親的前一刻,心中居然有些小慌張,這到底是為什麼呢?莫不是因為見不到他,心底有些慌嗎?
嗯嗯,定是這個原因。他不在身邊,少商始終覺得不安心。
她從來不依靠他人,孤立自主慣了,卻不承想,如此冷靜理智的她,婚前也是有些膽怯和緊張的。
【婚前的彩蛋】
蓮房從床上將程少商拖了起來,將其按到木桶中,各種香噴噴的花瓣撒入浴桶之中,給少商來了一個豪華熏香的沐浴。
少商坐在浴桶之中,看著五顏六色的花瓣,委委屈屈地望著蓮房:「蓮房,這太夸張了吧。」
「不夸張,這花瓣浴能讓女公子渾身上下散發著清香。」蓮房笑呵呵地服侍著。
「霍不疑也會泡花瓣浴嗎?」少商抬眸,問道。
蓮房小臉微紅,嬌羞地說著:「女公子,蓮房哪里知道這些事情。不過,我卻從未聽過男人會泡花瓣浴。」
程少商皺著小鼻子,一邊玩著水,一邊嘀咕著:「這不公平,我香噴噴的,若他還是一身汗臭我,我豈不吃虧了。」
「女公子,你莫要再說下去了。快快沐浴吧,女君正等著給您梳妝打扮呢。」蓮房打斷了程少商的話,想著若是讓她繼續說下去,還說不定會說出什麼樣的話來,她還是未出閣的女娘,真的是不好意思聽這些閨房之事。
蓮房幫少商沐浴后,便將其帶到了主廳,蕭元漪早已在此候著,看著亭亭玉立的女兒,想著她馬上便要嫁為人婦,鼻子突然一酸,心中說不出的難受。
她端著自己親自為嫋嫋做的糕點,略有些諂媚地上前,說道:「嫋嫋,快吃些糕點。
一旦上了花轎,新婦便沒有機會進食,該餓肚子了。」
嫋嫋面對阿母的熱情,始終覺得有些尷尬,她淺淺一笑,拿起糕點吃了起來。不知為何,她突然間懷念那個打她罵她的阿母,那時的阿母意氣風發,自己雖惱她,厭她,氣她,但是現在回想,那時的時光卻說不出的幸福。
眼前的阿母,溫柔許多,端莊許多,不再打罵自己,甚是還刻意討好自己,看著面色憔悴的阿母,程少商說不出來的心疼。她突然上前,抱住了阿母,將頭靠在了她的身上,弱弱地說了一句:「阿母,余生很長,我們都要好好地做自己。」
蕭元漪微愣,一時間不知所措,女兒這句話是何意?她是寬宥自己了嗎?
蕭元漪甚至不敢去問女兒,你可愿意寬宥阿母?面對女兒,她終究是有些愧疚和心虛。是呀,余生很長,大家都要好好地做自己。
蕭元漪緊緊地回抱了女兒,什麼都沒有說,直到女兒從她懷中掙脫出來。
她握著少商的手,說道:「坐好,阿母幫你梳妝。」
少商點了點頭,坐在了銅鏡前,乖巧地任由阿母替自己梳妝打扮。
她看得出來,蕭元漪并不擅長梳頭打扮,她拆了又梳,梳了又拆,手并不是很麻利。
蓮房看在眼中,想要上前幫忙,卻被嫋嫋給制止了,她知道,這是蕭元漪作為母親的一個心愿,她不想讓她難堪。
蕭元漪足足利用了兩個時辰,方才幫嫋嫋梳妝打扮完畢,又親自幫她穿戴好新婚禮服,能夠親力親為,這讓蕭元漪特別的滿足。
程始以及程家兄弟忙碌完瑣碎之事,帶著糕點趕到了嫋嫋房中,見蕭元漪正細心地幫嫋嫋戴發釵,程始笑著道:「夫人果然手藝高超,這裝扮完,我家嫋嫋立刻像個傾城傾國的大美女了。
」
程少商委委屈屈地看著程始,質問道:「阿父,難道只是像嗎?」
程始意識到說得不對,連忙改口:「不是像,就是,我家嫋嫋就是傾城傾國的大美女,倒是便宜了霍不疑那廝了。」
秧秧端著果子和糕點走到嫋嫋身邊,笑著道:「快吃些糕點,免得餓。」
少商拿起一塊栗子糕,甜甜地笑著:「還是堂姊懂我。」
程少宮走了上前,將一張饃遞給了少商,說道:「這是你家霍將軍托我轉交給你的,怕你餓。」
少商聽見是霍不疑給的,立刻奪了過來饃,小心翼翼地揣在了懷里,露出了滿意的笑容。她就知道,他最懂她。山珍海味,皆不如這一張饃。
程少宮見少商笑容滿面的樣子,忍不住吐槽:「瞧你一副沒出息的樣子,霍不疑一張饃,便讓你如此滿足。」
「你一個孤家寡人,你懂什麼懂?」少商笑嘻嘻地回懟著。
程少宮委屈地看著程頌,還未等抱怨,只見程頌摟著萬萋萋,點頭應允:「嫋嫋說得對,你也老大不小了,是該成親了。」
「我才不要娶妻,青山綠水如此美好,為何要將自己困在籠中呢?」
「拉倒吧,我看呀,是沒人肯嫁你。」少商笑呵呵地調侃著。
程少宮剛要反駁,只聽蕭元漪嚴肅地說著:「待嫋嫋成親后,是該替你議親了。」
程少宮哪里敢反駁阿母,不服氣地站在程頌旁,不敢言語。
少商挑釁地看著程少宮,一副調皮的模樣,蕭元漪見狀,心中舒坦許多。
天曉得,自從嫋嫋變得沉穩后,她的心跟著揪著疼,今日見她臉上又有了昔日的笑容,她也跟著放心許多。
解鈴還須系鈴人,霍不疑才是嫋嫋的真正心結所在之處。如今,兩人成親,也算是圓滿了。
【婚禮現場】
霍不疑身穿紅衣,高坐在馬背上,迎娶少商。
熱心腸的樓垚,原本打算將婚房設在樓家,可是,卻遭到了霍不疑的反對,他義正詞嚴地說著:「少商是樓垚的義妹,接新婦理應在樓家。」
何昭君笑笑不語,暗暗指責樓垚就是一個沒心眼的人兒,霍不疑怎麼可能會同意將少商娶回樓家,雖樓垚坦坦蕩蕩,但霍不疑自是不會允許這件事情發生。
最冤枉的要數袁慎,他本想作為娘家人送少商出嫁,卻也遭到了霍不疑的反對。想著他在西北數次幫助袁家,理應霍袁兩家更為親近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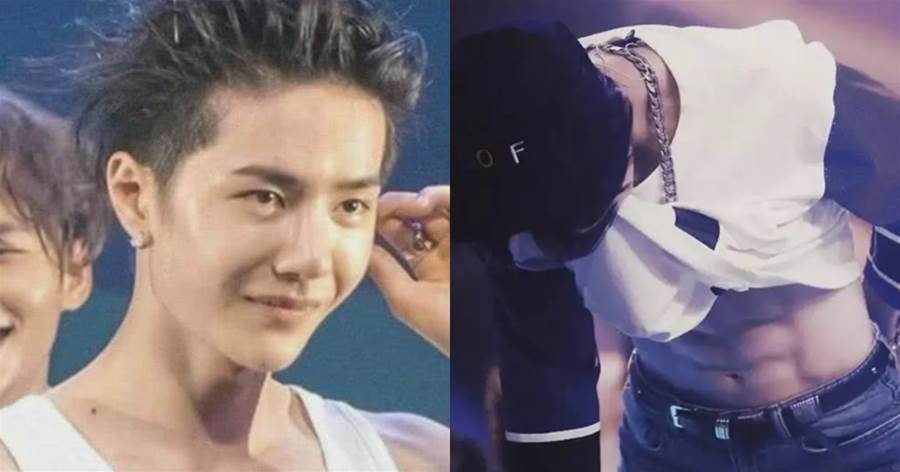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