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新婚夫婦倆,鬧了一些別扭。
霍不疑惱少商居然無緣無故將他拒之門外,當然,他渾然不知,少商乃是因為晨練的事情與他暗暗較勁。
一來少商真的是不想繼續這高強度的訓練,二來少商是真的沒有精力去搭理他,白天訓練那般辛苦,夜間哪有精力陪他顛鸞倒鳳。
昨夜沒有霍不疑鬧騰,少商難得睡了一個好覺,整個人都神清氣爽。
最重要的是,今日的她,睡到了自然醒,這簡直就像做夢一般。
大夢初醒的少商,沒有看見霍不疑的身影,心中有些疑惑,這人跑哪里去了呢?
好吧,她仿佛忘記了昨夜她鎖門的事情。
當然,鎖門這個動作,不過是少商的一個玩笑罷了。她太了解霍不疑了,那個門怎麼可能防得住他呢?他是誰呀,別說一道普通的門,就算是一道石門,他若想要進來,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。
只是她沒有想到,霍不疑這次居然當起了正人君子,沒有走「歪門邪道」的路子。
不過,少商依舊沒有將這一切當回事,只當他是良心發現,終于不叫自己晨練了。
用早膳時,少商依舊沒有看見霍不疑,她也沒有想那麼多,只當是霍不疑有事在忙。
沒心沒肺的樂觀派少商,用完早膳后,便在府邸閑逛,想著再完善一下府邸的修建工程。
阿飛看著精神百倍的少女君,想著今早黑著臉的少主公,兩人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,阿飛不禁感慨,這少主公的家庭地位堪憂呀。
想著自己陪著少主公操練了一整晚,他心中便覺得恐慌。
不行,不能讓少主公和少女君繼續生悶氣了,否則遭罪的只能是他。
想到這里,阿飛立刻走上前,與少商打招呼:「少女君好。」
少商看了一眼阿飛,問道:「阿飛,你家少主公今日很忙嗎?怎麼一直沒有看到他呢?」
見少女君一副茫然不知的模樣,阿飛越發覺得自家少主公太丟人了,只知道生悶氣,他無奈地嘆了一口氣說道:「少女君,您不要忍少主公生氣了,他一生氣,便睡不著覺。」
少商驚訝地看著阿飛,說道:「我何時惹你家少主公生氣了?非明是他氣我,我不同他一般見識。」
阿飛替自家少主公抱不平:「你將他關在屋外,害得他操練了一晚上。」
「阿飛,你這便是冤枉我了。以你家少主公的能力,誰能將他關在門外,除非他不想進來。」少商急匆匆地替自己解釋著。
阿飛弱弱地回道:「別人不能,但是少女君您能呀。您又不是不知道,少主公一向尊敬您,不敢違背您的意思,生怕您又說他拿權勢壓迫您,讓您的生活不自在。」
少商心頭一頓,阿飛的抱怨聲,讓她意識到,自己竟然無意間給霍不疑帶來了這麼大的壓力。她心虛地看著阿飛,小聲地說著:「我哪里有那麼不講理,不過是年輕氣盛時的氣話。」
「少女君的氣話,少主公可是走了心。少女君,你不妨去少主公軍營中的書房瞧一瞧,你便知曉少主公的心了。」阿飛說道。
少商心中不解阿飛為何要這般說,便尾隨阿飛來到了霍不疑軍營中的書房。待她走進,只見自己當年給霍不疑繡的鴛鴦盔甲高高地掛在書桌前,書桌上還放著自己當年所繡的金絲戰衣。
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那對鴛鴦盔甲上面粘貼了一張字條,醒目地寫著「鴛鴦」二字,仿佛在提醒著眾人,這是鴛鴦,不是雞。
這一幕,在外人眼中或許滑稽可笑,但在少商眼中,卻感慨萬分。
她弱弱地說著:「我以為這盔甲早就破損了呢?」
阿飛說道:「怎麼會破損呢?少主公邊疆流放的五年間,從未穿過這件盔甲,生怕損壞了。」
「他怎麼這樣傻,盔甲壞了,可以再做,人若是受傷了可怎麼辦?」少商傷心地說著。
「那時少主公以為自己和少女君再無可能,這盔甲是少女君留給少主公的唯一物件,他怎麼舍得讓它損壞呢。我記得那時,少主公每每上戰場都要親自刷洗這盔甲,并且囑咐過我,若是他戰死,定要和這盔甲、金絲戰衣合葬。」
少商撫摸著鴛鴦盔甲,傷感萬分。
「這對鴛鴦盔甲便是少主公的命,軍中將領但凡有人錯叫成雞的,少主公都要罰他們板子。後來,不想別人叫錯,少主公更是直接將鴛鴦二字貼在盔甲之上。您不知道呀,曾有一段時間,軍中將領一度懷疑少主公受到了刺激,神志不清。」阿飛說著說著便笑了,回想往事,倒是有些滑稽。
少商扯下了「鴛鴦」二字,喃喃自語:「那時繡得屬實有些難看了,以至于那麼多人認錯。」
阿飛笑著道:「少女君放心吧,您繡得難看,少主公也喜歡。」
阿飛真誠的話,得到了自家少女君的一個白眼,臨行前,還不忘瞪了他一眼。
他不懂,有些話,女人自己可以說,但是外人不可以說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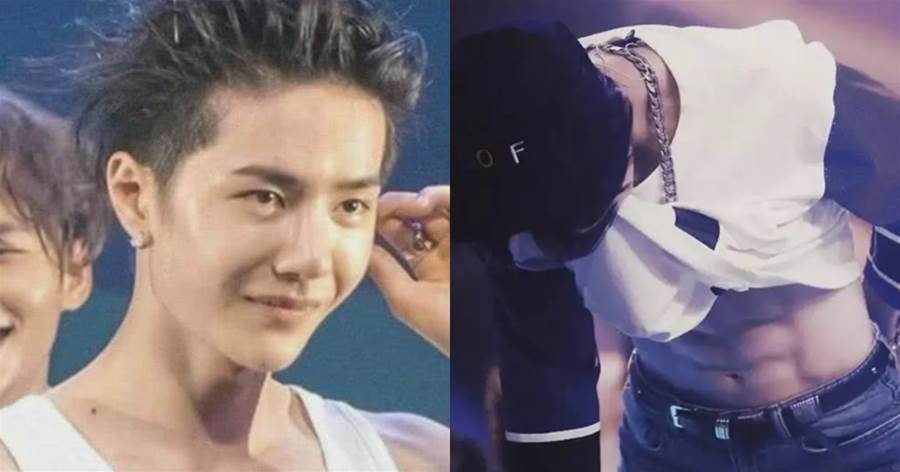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